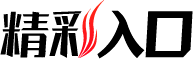文化之窗|启功为何涂抹改写这幅题字
大众日报记者 于国鹏
2022-07-26 07:29:00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前几天,启功先生所题“张大千纪念馆”匾额的照片被网友贴到微博上,又引发新一轮讨论。这幅题字之所以引发热议,因为这六个字里有两个字被涂抹重写了。网友讨论的焦点,一是启功为什么要涂抹改写,而不是重写一张?二是对于书法家在作品上直接涂改这种现象应怎么看?
先说引起大家广泛争议的这幅题字。启功先生应邀为“张大千纪念馆”题写馆名,他欣然命笔。但这件作品并非一挥而就。题字为横幅,用繁体字自左向右写成,其中“念”和“馆”二字都是涂抹后重新写成。最后有启功先生落款“启功题”,并钤红色印章。
从整体看来,启功先生应该是在写完六个字后才进行了涂改,因为新写的“念”字在原字右下方,新写“馆”字在原字后方。显然,如果是刚写到“念”字即觉不妥,继而马上涂改,那么从整齐美观的角度来说,新写的“念”字应该是放到所涂掉“念”字的后边,排到整齐的一行里。放到右下方,只能是因为后边的“馆”字也已经写完,两个字之间的空间不足以容纳同样大小的一个字了。而“馆”字被涂掉后,就是接着在后边一个字的位置重新写成。
按说,书法家写漏字又在旁边补足,或者写错字后进行涂改,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就是王羲之兰亭雅集酒后所写,颇如行云流水,得自然之天趣,正因此种随意,中间有颇多涂改增删之处,如“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初写时即无“崇山”二字,后又在旁边补上。天下第二行书即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同样也有多处圈点涂改。但是,这两件作品从来没因此起过什么波澜。
启功这幅题字,为何引发那么大的争议呢?首先,这幅字是应邀题字,不是个人随意写点诗词歌赋,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其次这不是什么长篇文字,只是简单六个字。正因此,涂改到如此严重程度,就让人觉着不太合常理。自然就不断有人揣测,启功先生这么做是否有特殊的原因。
还有人更进一步认为,最后的“馆”字不仅涂改了,而且是写了个错字。在这里,启功先生写的是繁体字“館”。网友认为,应该写作“舘”,因为“館”是指吃饭的地方,而“舘”才是指用于休息或展览之处。这种说法,更引起大家兴趣:启功先生不仅是一位书画家,也是一位在中国古典文化领域有很深造诣的学者,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堪称大家。他怎么会犯这么幼稚的错误?
在这些猜测中,有一个观点让很多人觉得有道理。据此观点解释,启功先生是有意为之,也就是说是故意涂抹的,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以此种方式表达对张大千某些品行的不赞成,是以此种方式来调侃或者挖苦张大千。那么,他对张大千哪些品行不赞成呢?网友又提出了多种说法——要是按这个方向去理解,启功先生涂改的恐怕就不只是两个字了。
为此,《书法报》专门在“观点”版组织了一期文章,刊发业内专家对这件事的看法。书画家李庶民在文章中写道:“我认为,从启功先生的处世为人、功力学养以及此件作品的落款、钤印的认真规范来分析,既不是写错了随意涂改,也没有写错字,更不是故意调侃张大千,而是对写好后的六个字中的‘念馆’两个字不太满意,故又重写。对比之下,后写的为优,遂将先写的涂抹掉了。”
同时,李庶民引用《说文解字》注释,“馆”乃“客舍”之义,并引用唐代韩愈文章中的使用,来证明启功用“馆”之无误。他表示:“至于还有人愣装明白,说什么启功先生‘馆’字错了,应写作‘舘’,则更是妄议。”
另一位书画家安昌礼则表示,“以笔者浅见,应为启功先生考虑到此字是制作牌匾之用,对所题之字或觉不够满意,于是怜纸惜墨涂改补题,故书写字样以集字出现,没成想纪念馆单独裱挂珍藏。”
对于所题“館”字之正误,安昌礼认为,“‘館’是否应为‘舘’也不尽然,因古文字相互替代之多矣。”
显而易见,两位专家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这就是启功先生率性而为,且存怜纸惜墨之举,而并无调侃或者讽刺之意。安昌礼还特别写道:“凭启功先生的学问,德艺双馨、师为世范、蔼然仁者、菩萨心肠,万不可能在已应允题字时挖苦另一位与自己比肩的艺术大家。”
我曾在网络上看到过很多回忆或者介绍启功先生的文章,这些文章作者大都是与启功先生有长期交往的朋友,他们也多获启功先生墨宝相赠。在文章中,他们也大都会把启功先生所赠书法作品一并贴出来,供大家观赏。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在启功身上确实很常见。
比如,他曾给北京师范大学九四届毕业生题字“教学相长,勤深业广。无限前程,莫负理想!”这幅作品,竖排,每排三字,共五排。其后是题款及钤印。但是,问题来了,三字一排,共五排,只有十五个字,而原文却是十六字。再检视一遍,原来漏写了一个“限”字。启功先生直接在“无”字下边补上一个小一些的“限”字。因为根据书法规矩,补字要小于正文。启功把这个补写的“限”字写得比正文小,但跟题款差不多大,整体看上去,倒也并不妨碍整幅作品的布局与美观。
启功曾为北师大曹文翰题字,也出现类似一幕。这幅落款写着“曹文翰同志从事摄影工作三十年题此为贺 启功”的作品,写正文时也漏了字。关于这件事的具体经过,《北京师范大学校报》的副刊《京师学人》曾对当事人曹文翰进行采访,进行过详细报道:他(指曹文翰)对启功先生最熟悉,总说启先生乐观、随和。“我一拍照他就老逗我‘装胶卷了吗’。有时候边拍照片他还边在说话,不看镜头”。老曹摄影三十周年时,启先生为他题了一首诗:美好生活,秀丽山河,镜中世界,画上笙歌。老爷子边说话边写字,写完后一读才发觉有点不对劲。“哎!怎么落了个‘河’字。后来就在旁边一勾,填了个小小的‘河’字。他还说毛主席经常有这个情况,填上更真实。我一听他把毛主席都端出来了,就不好意思让他重写了”。
启功先生就是这么豁达幽默。他的幽默是骨子里的幽默,不说别的,听听他的一些学术讲座,讲到某些情节某些段落的时候,就如同听单口相声,一个个“包袱”抖得恰到好处,常逗得听众开怀大笑。曾有人在路上遇见他,关切地问候,近来身体怎样?启功先生一本正经地回答:鸟乎了!这回答让对方有些发蒙,“鸟乎”是个啥意思,从来就没听说过这词,就再求解释。启功回答:就是差一点乌乎了!双方会心大笑。多了解一下启功先生的这些故事,会对他的这种“段子手”个性有更深刻的了解,也会对他对于书法的态度有更多了解。
再回到启功先生所题“张大千纪念馆”。我认为,李庶民、安昌礼等专家的分析都是准确的,启功先生这种举动,并没有太多深意。一方面,兴之所至,信笔挥洒,他对作品整体很满意,发现某个字没写好,然后涂掉重写,或发现漏字后补足,可能算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否则,整张重写未必能重现这种状态和激情,未必能写得那么好,消耗那点纸墨倒还在其次;另一方面,这也肯定与启功先生豁达幽默的个性有关,他这种性格作出这种处理方式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如今,在各种展览或其他场合,我们很少会看到像启功先生这样涂改过的书法作品。一般说来,书法家创作完成一件作品,感觉有瑕疵,往往是直截了当地重新写一件。近几年,山东承办过多次国家级的书法展览或者书法大赛。在这种级别的赛事中,当然不会看到有涂改内容的作品,因为这首先就不符合参评参赛条件。但相关评委介绍展览概况或者参展参评作品的时候,常会听到有这样一种情况,某件书法作品艺术水准不错,但因为中间出现了错别字,最终遗憾地被淘汰了。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书协原主席沈鹏曾经说,有的是因为别字和异体字混在了一起,还有的是因为书写随意性导致的。他特别指出:“写错别字比较多的情况,是把简体字还原成繁体字。如皇后的‘后’,后羿射日的‘后’,还原成繁体字‘後’,就出错了,这是不能还原的,须知那‘后’并非繁体字的简化。”
像启功先生这样,率性而写,写完后感觉不满意又率性而改,且坦然处之,不怕示之于众,并不失其风度,也不失其作品之风雅。倒是错别字的问题值得关注,书法作品里出现错别字,无论改或者不改,都有些风雅扫地了。(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于国鹏 报道)
责任编辑: 吕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