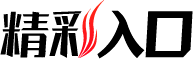我的孝亲之年|书架前的温暖旋律
大众日报记者 范薇
2022-02-13 07:04:57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春节回家,和父母一起完成大扫除的收尾工作。擦拭书架,拂去整齐排列的书籍上的灰尘。小时候爱不释手的《儿童文学》,中学时最喜欢读的诗集……就像一位位久未谋面的老友,再会时依然向我露出会心的微笑。这里大部分书虽说已有些年头,但在家里人的悉心打理下封面仍色泽不减,正衬得角落里的几个灰扑扑的书脊格外不同。以前我也并非没有注意到它们,只是心里下意识地将它们认定成无聊的大部头,或是地摊上买来的没营养的读物,从来没有仔细看过。但这次,我不由自主地将它们轻轻从书架上取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本《巴黎圣母院》。软纸的封面只比内页稍厚,仅有两色的花纹装饰。还有一本只剩灰色的硬纸壳封面,大概是外面包的书封已经丢了,翻开来才知道是贾平凹的小说。还有三本更薄的书,它们开本相同,书脊都已泛黄,上面的字也模糊不清。从保存得比较好的一本上,我看到这竟是初中语文课本。小心地将它们取下,将破损处拼接在一起,完整地看到了它们的“真实身份”——不同学期的几本初中语文课本,来自二十世纪80年代。我上初中时的语文课本,有精美的图案印刷在覆膜的封面上,而现在手里的课本,软纸封面已是起毛、卷边,仅在右下角印了一朵单色的花。翻开内页,课文中用隽秀的字体做了标注和笔记,课后问题也整整齐齐地作了回答。从印刷的年代看,这几本课本应当是我父母用过的,而手写的字体告诉我它们应该属于我妈妈。
我找来胶带,把封面开裂的地方粘起来,卷起的书角也贴上胶带使其变硬而不再翘起。但别看封面伤痕累累,内页还是比较平整,也看不到随意涂画的痕迹,甚至连画线也用了尺子,无一不是笔直的。稍作修补,课本的外观又变得板正。看来,爱惜东西是妈妈从学生时代就培养的习惯,她现在的梳子已经用了十余年,光泽如旧,没有摔断一个齿。回想我曾经还没过完一个学期就少了封面一角的课本,不禁感到羞愧。
我把修补了的课本拿给妈妈看,她见我拿着这些课本,先是“责怪”了起来:“又从哪里扒拉出来破烂东西了,快收拾好。”随后却接了过去,翻看、抚摸,喜上眉梢。她指着做笔记的地方说道:“当时我听讲多认真,还是当学生的时候心态最诚恳。”妈妈在沙发上坐下,仔细翻看,忽然指着一页对我说:“这篇课文我特别喜欢。”我凑过去看,是名为“金色的鱼钩”的一篇文章。“草地”“老班长”“鱼汤”等词汇,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这也是我小学时学过的课文。妈妈好像还记得文章内容,看了题目就说了起来:“老班长舍己为人,把鱼汤让给生病的小同志,自己却牺牲了。哎呀,看得我都掉眼泪了。”在妈妈的讲述下,当初的那份感动又回到了我的心上,也许她也有同样的感受。我坐在妈妈旁边,看她翻看课文,听她说以前学习的感受,又说起上学的趣事。她告诉我以前老师是怎样用油印机印卷子:用蜡板垫底,用圆珠笔把试卷的内容刻在蜡纸上,拉动油印机的油墨辊,一次印一张卷子。如果技术不过关,就会弄得到处是黑乎乎的油墨。

言谈间,几十年的时光仿佛从我们身边悄悄走过,又将她带回了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那时的生活,各方面的供给虽然不如现在丰富,但多年以后仍是一段甜蜜的回忆。曾几何时,我热衷于向父母解释时下的各种流行语、流行文化,以为像这样就等于让他们跟上年轻人的步伐,就能让他们感到快乐。但他们有时表现出的为难也让我困惑。也许现在我找到了答案,与其全力将他们推向新兴事物,不如也时常陪他们聊聊天,听父母讲讲那过去的时光、如歌的岁月。和他们一起捡拾失落在时光里的回忆,更了解与我们最亲近的人,本身也会成为生命里一段温暖的旋律。
责任编辑: 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