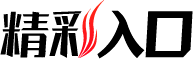说古论今丨当作情书这么写
大众日报记者 于国鹏
2023-05-30 06:57:58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前几天,在应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朋友,欢迎回家——剧作家活动日”时,著名作家刘恒在发言中谈到了自己对职业、对创作的热爱。这些话平凡、普通,但耐琢磨,能让人感受到他的深厚感情,受益于他的真知灼见。
刘恒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北京老舍文学院院长、《北京文学》主编。他虽然自谦“一个过气的小说家和编剧”,事实上,他近年来一直保持着活跃的创作状态,不断有新作推出,这些作品都很有分量,称得上重头之作。
创作业绩成就了他在文艺界的地位和影响。1986年,他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获第8届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让他蜚声文坛。这个作品迅速成为很多高校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的学习研究内容。1990年,根据刘恒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电影《菊豆》上映,刘恒担任影片编剧。《菊豆》由张艺谋执导,巩俐、李保田等主演。电影上映后,吸引了海内外关注,后来又成为第一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的中国内地影片。
此后,刘恒陆续出版长篇小说《黑的雪》《逍遥颂》《苍河白日梦》。在坚持小说创作的同时,他编剧了多部电影作品,除了《菊豆》,还包括《本命年》《秋菊打官司》《红玫瑰与白玫瑰》《画魂》《没事偷着乐》《漂亮妈妈》《张思德》《云水谣》《集结号》《金陵十三钗》等,还编剧电视剧《大路朝天》《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少年天子》,话剧《窝头会馆》,歌剧《夏日彩虹》等。
这些优秀作品为他赢得了数不清的荣誉。他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老舍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最佳编剧奖、飞天奖优秀编剧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华表奖优秀编剧奖、第35届瓦亚多里德国际电影节金穗奖、第6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提名等。看着他好像信手拈来,其实哪个难度都很高,足以令实力一般的作者望而却步。
能创作出这么多优秀作品,获得这么多沉甸甸的荣誉,他有何秘诀?从刘恒在“剧作家活动日”的发言中可以沿波讨源,找到答案。根据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微信公众号剧本编辑部推送的报道,刘恒在发言中说:“分析自己踏入这个职业,踏入这个行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呢?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热爱,热爱这个职业、热爱这个技能。”热爱,给他的创作开拓无限空间,也为他的创作孕育无限可能。
他到底热爱到什么程度呢?他这样表达:“我把我生命某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接一个段落地贡献给一个又一个剧本,我觉得我活得非常值。我觉得不光人生是一个剧本,我们的每一个剧本也都是有生命的,一个完整的生命。他们就像我们一个又一个孩子,不管美也好、丑也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是从我们的血液里滴出来的,无比珍贵、无比可爱,而且无比高贵。这是我对我职业的看法。”
这种热爱可谓深入骨髓,刘恒称之为“埋藏在基因里的”。他特别举例,小时候,因为特殊时期各种条件限制,受到的教育有限。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并没有影响他对艺术的热爱。那个时候,在小学生练字的横格本上,他开始尝试着写小话剧。看一场电影,感动之余,回到宿舍后,他会打着手电筒,把这些记到横格本上,把自己记住的台词记录下来。
读刘恒的小说,看他编剧的影视剧,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他作品里的那些人、那些事令人印象深刻,主要在于他对生活的深刻观察高人一筹,他对社会本质的揭示高人一筹。而他能在这些方面高人一筹,正是因为对文学创作这种发自心底的热爱。这种热爱给了他创作的不竭动力,无疑也给他增添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手中的这支笔,面对着更大的挑战。这时候,对他来说,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不再是简单地过日子,既要用心体会和感悟自己这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又要用心观察和思考周围的人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这让他心甘情愿地走进生活更深处,走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那些角落。换句话说,在热爱的前提下,他的创作实现了通俗性基础上的深刻性。
对于这些问题,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研讨和解读,也让我们对刘恒及其创作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唐宏峰在评论《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时谈到,生存困境是刘恒执着表现的主题,这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写实小说”的影子还在。“刘恒在小说中有意隐匿精神需求,凸现当下的物质存在,专注于普通百姓最低生存欲求,悬置判断,向形而下层面不断挖掘。小说利用张大民的贫嘴,细细致致地把一切生活琐事的卑微与尴尬展现出来。比如张大民比较他和云芳的夜班费,在两毛钱差别和夜宵馄饨馅多少中反复计算平衡,让人忍俊不禁又心生苦涩。”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对生活的丰富了解与体验,这种细节是写不出来的。这种生活背后的人的生存困境,如果没有深入思考与独到认知,也是无法写深写透的。写城市生活,刘恒很拿手。他是北京人,对北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自然十分熟悉,无非是“老字号、四合院,门槛、门墩,遛鸟儿、走票,下棋喝茶、胡侃神聊,以及由这种生活养成或者说是养成这种生活的性情格调”。正是熟悉这种生活场景,熟悉这种生活情调,并且有他独特的观察视角,才会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对普通人生活绘声绘色的描绘和展现。
刘恒还有许多作品,如《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都是表现农村生活的。在这一类作品中,描述的场景非常生动,使用的语言也都非常朴实、鲜活。刘恒又是如何做到的?其实,对于农村生活,他毫不陌生,且十分熟悉。他曾经提及,自己的父母是农民,后来进城讨生活,逐渐在城里站稳脚跟,这也让他与那个乡野小村有了“无法斩断的联系”;刘恒在中学还未毕业时即到农村插队,所去之地正是父母的故乡。在那里,他和村民们一起劳动,一起挣工分。他真正深入到农村的肌理之中。所以,文艺评论家朱伟说:“他像熟悉自己身上每一个器官那样熟悉农村。他能深切地感受农人生存的窘迫,能想怎么表演就怎么表演。”
翻一翻文学史,我们不难了解,那些文学家和艺术家走上文艺之路的原因虽然五花八门,但相当一部分确确实实是因为热爱。正因为热爱,他们不仅创作出很多流传后世的经典作品,留下诸多有关文艺创作的卓越见解,也留下许多令人回味无穷的趣闻逸事。唐代诗人李贺就痴迷于写诗。李商隐曾写过一篇《李贺小传》,记载了关于李贺写诗的一些故事。李贺外出,喜欢观察周围景物而入诗。他骑一头瘦驴,背一个旧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李贺写诗的这种状态,“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正因这样“呕心沥血”,李贺留下一大批优秀诗作。在文坛、诗坛、剧坛上,类似李贺者不在少数。还有一部分热爱文艺创作的人,最终成长为评论家、理论家。这些人在文艺批评领域卓有建树,其理念、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一些创作经验,直到今天依然被文学爱好者学习和遵循;他们指出的一些不利于文艺创作的错误观念,以及文艺创作中应当戒除的弊端,直至今天依然并不过时。
再回到刘恒。刘恒编剧的话剧《窝头会馆》搬上舞台后,刘恒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论是写小说、写剧本、写电影剧本、写话剧剧本,我所有的文字,都是写给最爱的人的情书。所有文字都渗透着我的爱。”像刘恒这样,把作品当成给最爱的人的情书这么写,想写不好都难。
责任编辑: 李文智